34年前的今天,切尔诺贝利从一个普通城市定格成为永恒符号。
表面上,世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森林地带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爆炸,喷涌出巨量放射性核素,造成数量成迷的人员伤亡和生物畸变,污染了1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影响波及840万人。危害至今仍存,并将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什么造成了它的发生?它与世界怎样关联?它如何被解决?当所有严肃的记录和反思将真相层层剥开,人们看到共存于苏联体制中的令人抓狂的体制性怠惰、系统性的隐瞒与欺骗,还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些,在切尔诺贝利事件里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事后来看,那场爆炸的确将苏联带向了不同的方向。许多事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苏联进入战时状态,但敌人看不见摸不着,它存在于空气中,水里,食物里,衣服上,战士攻击无力,无处可躲。
“鬼城”切尔诺贝利
一种新的时空感被触发了,国境的区隔与阵营的划分失去意义,核污染随着大气流动扩散至别国。在苏联向世界发出警告之前,它已先一步收到了来自瑞典的提醒。
一周之内,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瑞士、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希腊、以色列、科威特、土耳其、日本、中国、印度、非洲、美国、加拿大,几乎全世界都检测到高辐射剂量,它俨然已不是一国问题。
一时间,苏联国内阴谋论重嚣尘上,“西方情报机构”,“社会主义的死敌”,“间谍攻击”,“暗中破坏行为”,“背后偷袭”,“企图破坏牢不可破的苏联各族人民联盟”。苏联人无法描摹和理解看不见的敌人,重拾旧日话语,矛头直指间谍和破坏分子。
那些与英雄行为和牺牲精神相违背的,须保持沉默,图书馆里有关辐射,广岛和长崎,射线的书一同消失了。
切尔诺贝利内部,工作人员正在检测核辐射数值
坚硬的苏联体制被切尔诺贝利撕开一道裂口,靠隐瞒事故维持的几十年核安全神话被戳穿,官僚体系的推诿无能暴露于众。
曾经的骄傲化为恐惧,自信变为担忧,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在体制庇护下建立新生活,以无比的坚韧和乐观开始学习与核辐射共存。
在那些承受痛苦的时刻,他们一定曾一遍遍地追问,那场灾难是不是一定要发生?
事 故
回到那夜。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惊雷一般的响声划破夜空,大地震动,柱状的火焰向夜空喷涌,黑夜被照亮,天空变得色彩斑斓。
不少人注意到了爆炸,围观了突现于夜空的美丽景观,全然不知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
50吨核燃料蒸发为气态喷向大气中,以每小时30000伦琴的辐射量扩散开来,70吨混合着建筑残骸的核燃料散乱在地上,以每小时20000伦琴的数值持续向外辐射,而人体吸收400伦琴就足以致命。
直升机上拍摄的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
危险没有被察觉。休息的工人照常钓鱼,消防队员发现了火势,没有穿戴防护装备就赶来救火,好奇的孩子找到视野开阔的地方张望,核电站当晚值班的工作人员懵了。
反应堆爆炸是最糟糕的情况,没人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也没人愿意相信。包括切尔诺贝利在内的核设施的安全性几乎无可置疑,它被形容为可以建在红场上的“茶壶”,甚至曾有人建议把核电站就建在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20公里处。
但安全只是个神话。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苏联可考的核电站事故已达11起。就在1982年9月,切尔诺贝利1号反应堆曾发生过堆芯部分熔化事故,放射性物质扩散到附近工厂和普里皮亚季镇——这个因核电站而兴的小城,维修人员也受到严重核辐射。
事故发生前的普里皮亚季镇
但事故被层层保密,哪怕对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所以之前的教训并没有对核电站工作人员提供警示。
4号反应堆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是当晚的主持者,他在核电站主任布留哈诺夫和总工程师福明的授意下,本意为测试反应堆的自我供电系统,提高核电站的发电量,节省能源,完成政治计划做准备。
但佳特洛夫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管理者,他来自实验物理领域,对核电站的热能布局不熟悉,对切尔诺贝利采用的铀-石墨型反应堆也不了解,他那来自电气化工领域的上司福明也好不到哪里去。
操作人员和管理者的不专业,在核电站并不鲜见,外行行政官员粗暴领导内行专业人员是体制内常态。
在迫切心态的驱使下,测试实验在凌晨展开,绕开了反应堆的安全系统,放大了它的设计漏洞。
事后,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中)被判处10年监禁,9年后去世
关于造成反应堆爆炸的物理原理非常复杂,简单来说,反应堆工作时需要正反应和负反应的平衡,正反应过高会造成过热风险,但切尔诺贝利采用的是RBMK反应堆(铀-石墨反应堆),其设计缺陷恰好在于,各项正反应因素的组合权重过高,使得爆炸的可能性天然存在。
设计人员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为此,反应堆被设计了紧急叫停按钮,按下按钮,控制棒插入反应堆,就能抑制正反应。
但要命的是,控制棒最下端的填充材料是石墨,石墨会加剧正反应,而非抑制正反应,所以当控制棒插入,反应堆首先会产生短时的正反应浪涌,正是这一设计缺陷,导致了本来是叫停操作的保命按钮变成了加速爆炸的送命按钮。
爆炸前20秒,负责操作的阿基莫夫按下“紧急功率降低”按钮,致命的是,控制棒未能正常插入堆芯,甚至还没降到一半就卡住了,能量瞬时上涌,爆炸发生。
而当值的核电站工作人员显然对这一设计不够了解,以致于他们到死都不明白堆芯为什么会爆炸,坚持认为自己的操作无误。
爆炸发生后,在现场主持的佳特洛夫完全没有考虑反应堆会出问题,他判断应急保护与控制系统的水箱发生了瓦斯爆炸,并无大碍,并向总工程师福明和核电站主任布留哈诺夫报告,反应堆安然无恙,一切正常可控,随后这一报告又上传到莫斯科。
收到报告的莫斯科据此作出错误决策,发回“向反应堆注水冷却”的指示,导致核辐射的进一步加剧。
仍在沉睡的普里皮亚季小镇,就这样在无知无觉中暴露于核辐射之下,长达两天之久。
扩 散
尽管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和通知,但核辐射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
爆炸几个小时后,当晚在河边钓鱼的几名渔夫开始感到极度恶心和不舒服,胸口灼热,眼皮刺痛,头疼欲裂,不断呕吐,黎明时皮肤已经变成黑色。
第一批赶到现场的消防队员被严重灼伤,送去医院。核辐射有潜伏期,初期症状是呕吐,腹泻,之后状况会加速恶化。
被送去医院的消防员一天一个样子,嘴里、舌头上和面颊上出现小块溃疡,之后逐渐蔓延,粘液层层结痂,体色逐渐变得乌青、紫红、灰褐,头发和皮肤不断脱落。
在核电站抢救的人越发感到不对劲,他们发现了散乱在地上的石墨块,口中尝到金属的味道,酸酸的,只工作一会儿就浑身乏力,筋疲力竭。
意外发生后,有203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31人死亡,当中有28人死于过量辐射
是核泄漏了吗?人们心中都有疑问,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核电站里,手边能找到的辐射测量剂最高只能测到每小时3.6伦琴,能测量1000伦琴的锁在保险箱中,被埋在废墟下,难以取出。
4月26日上午10点,强辐射已经持续了一夜,一期建设工程运行副总工程师西特尼科夫根据经验判断,反应堆已经炸毁,他焦急地通知福明和布留哈诺夫,但被愤怒地驳回,核电站民房部主任沃罗比约夫发出的强放射性警告,也被拒绝倾听。
向反应堆内注水的操作继续进行,而在每小时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辐射值在正常范围内”,“形势依然可控”。
但莫斯科坐不住了。4月26日上午9点,第一个专家小组从莫斯科贝科沃机场起飞前往切尔诺贝利,当天晚9点,分管能源口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尔比纳随着第二批小组抵达普里皮亚季,接管抢救工作。
政府委员会和专家团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有委员就住在普里皮亚季镇上吃住,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依然认为反应堆到5、6月就能恢复使用,但很快,委员们也都表现出了辐射症状。
消防员在扑灭三号机组周围的火
在初期,官方抢救工作就这样在一种看似紧张实则矇昧的状态中进行,而小镇依然处于平静之中。
4月26日是一个周六,春日明媚,普里皮亚季人的生活一切如常,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耍,他们虽然听到了前一晚的爆炸声,但并没有多少担忧,街头出现了戴着面具的士兵,民居不以为意。
但当天傍晚,空气中的辐射量就已经达到正常值的60万倍,按照辐射的扩散速度,只要4天,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吸收的辐射量就会致命。
核泄漏的消息通过不同途径陆续传来,男人们开始喝伏特加给自己消毒,还有喝洗洁精的,但喝了腿发软。食物全被污染,要么吃下去,要么饿着。有些人的皮肤颜色慢慢变深,情绪变得激动。
4月27日,政府的疏散行动终于开始。1100辆客车沿着从普里皮亚季到切尔诺贝利将近20公里,下午1:30,客车开动,在每一栋公寓前停下,接走楼里的居民。
从3号反应堆的屋顶上俯瞰4号反应堆受损建筑
居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打包,他们被要求轻装上阵,只要带三天的食物和钱就好,人们互相安慰着上车离开,与自己的宠物道别,不知将就此永远地离开家园。
上了年纪的人无法理解正在经历的一切,为什么必须要离开呢?土地还在,万物仍旧生长,花儿也在开放,有老人坚持不愿离开,留了下来,几天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普里皮亚季没有毁灭,它被急匆匆地遗弃,成为一座空城。
抢 救
反应堆的大火还在燃烧。问题的严重性愈发明显,国家机器开动了,动员机制一并启动。
首先要灭火。谢尔比纳提出用消防艇向燃烧着的反应堆内喷水,所幸被专家阻止,改用沙子和硼酸灭火。水无法扑灭核能火焰,蒸发后与核能燃料混合,还会增加辐射,污染周围的一切。
上百架直升飞机从基辅开来,飞到反应堆上空,由士兵徒手把80公斤的沙包扔下。
任务无比危险,飞机飞得太高,扔下的沙土会激起更高辐射,他们要暴露在夹杂着放射性气体、离子以及伽马射线的热浪中工作,刚开始执行这项任务时,没有人带呼吸器,也没有真正的防护。
飞行员在投放混有硼酸的沙子给反应堆灭火
与此同时,另一组三千多名士兵走上房顶,暴露在每小时上万伦琴的辐射环境下,充当人体机器,把炸开的石墨与核燃料铲进反应堆大坑中。
为了防止高温的反应堆燃料熔穿底部进入地下,上万名矿工被动员来到切尔诺贝利施工,他们要从三号反应堆挖出150米的地道到4号反应堆,在4号反应堆下挖出长宽各30米的空间,以注入让反应炉降温的冷却装置。
在普里皮亚季,留守的军人徒手捡起地上的石墨块,因为没有机器人手臂,士兵们的皮肤变成了褐色,呼吸器挂在脖子上,却没有人戴着。
抢救紧张地进行,虽然问题再难以隐瞒,但国家仍旧试图保持正常姿态,乌克兰的五一节日游行如期举行。
游行队列里有人不解,大胆发问:“我们受到多少剂量的辐射?为什么隐瞒?”后来他被部队指挥官叫去,被训斥“制造紧张气氛”。
当年的清理者(摄影/Lgor Kostin)
防毒面具发下来了,谁也没有戴。
5月6日,莫斯科召开b·体育(中国)发布会,谢尔比纳主持会议,苏联国家气象委员会主席尤里·伊兹拉埃尔和副主席谢杜诺夫,就核爆炸的严重性一笔带过,称被摧毁的反应堆周围的辐射值只有每小时0.015伦琴,而当时仅普里皮亚季的辐射值均就在每小时0.5至1伦琴。
5月14日,灾难发生后第18天,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人民发表演说,承认了切尔诺贝利发生的灾难,表示“核能脱离了人类的掌控”。
此时,苏联以举国之力投入对灾难的抢救之中,十万名官兵投入进入切尔诺贝利,组成清理人大军,清理放射性物质。
许多普通市民打电话到能源部,要求前往切尔诺贝利,帮助战胜那里的灾难。危机时刻,他们只希望为国家做些什么,最终,总共约60万军民投入对切尔诺贝利的抢救之中。
清理反应堆屋顶的石墨,每人只能工作40-60秒
但物资严重不足,士兵们领不到充足的防护用品,只能自己动手缝制铠甲、铅衬衣,铅内裤。
在投入几十万人,花费180亿美金的努力下,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上建立起密闭的石棺,而参与抢救的清理人大军中,后来统计有2万人死亡,20万人残障,四分之一的矿工在40岁前去世。
当时规定士兵受到的辐射超过二十五伦琴就算过量,超过辐射量指挥官将受到惩罚,最后,没有一个人的辐射量会超过二十五伦琴。
在公众中,切尔诺贝利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7月18日,苏联能源于电气化部长马约列茨发出指令,严禁下属在b·体育(中国)报道中,广播中或电视上讲述关于切尔诺贝利的真相。
生 活
“人们在排队买面包、食盐、火柴……这样的感觉便更加强烈。人们都在忙着做面包干,每天要把地板洗上五六次,还要填上窗户的缝隙。大家整天都在听收音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下了当年的核灾难亲历者的生活,灾难放大并袒露了人性中的幽微面目,令人感叹。
乌克兰女人在市场叫卖大红苹果:“来买苹果呦!切尔诺贝利的苹果!”有人劝她不要这样叫卖,没有人会买。“别担心!”她说,“还是有人会买的,有些人要买给丈母娘,有些买给老板。”
事故发生后,在切尔诺贝利地区生活的狗
大家互相吓唬。有人在市场买了一顶狐狸皮帽子,头就秃了。有亚美尼亚人从“坟场”买回一把便宜的冲锋枪,就死了。
巫师流行,他们宣称自己能让一百公顷土地上的锶和铯加速衰变。报纸上对他们大加报道,电视给他们黄金时段。
公交车上,一个男孩没有给老人让座。老人说他:“到你老的时候,别人也不会给你让座。”
“我不会老。”男孩子回答。
“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快死了。”
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截图
女人们把伏特加通过注射器灌给自己的丈夫,以此叫他们安静。
离开家园的切尔诺贝利人因为“被污染了”,到处被拒绝、被排斥,他们睡在学校和俱乐部的地板上,无处可去。
上学的孩子哭着跑回家,学校里的同学都害怕,不愿挨近他。他们被叫做“亮晶晶”“切尔诺贝利刺猬”“切尔诺贝利萤火虫”,去到任何地方,都被当作活着的怪物和嘲笑的对象。
死在莫斯科医院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放在焊死的铅质棺材里,埋在莫斯科郊外的米京墓地,其他人都不愿把死者埋在他们的旁边,想要躲开。连死人都害怕切尔诺贝利的死人。
切尔诺贝利人渴望被世人知道,又害怕被报道,他们在灾难面前歇斯底里,或陷入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在承受突然降临的痛苦,成为傲慢与谎言的代价,尽管他们并没有任何错误。
要说真话,要保持敬畏与审慎,这是切尔诺贝利留给后人的警示。理解这警示的分量,是每一个活下来的人的道德责任。
参考资料:
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 《亲历切尔诺贝利》
阿列克谢耶维奇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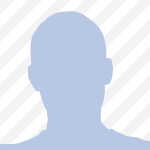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