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愈加明白“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道理,只要有空我就去父母那儿看看,有时晚了就住在那里。
清晨,天色微明,我每每在半梦半醒状态,便能听到一声鸟鸣伴着第一缕曙光从厚重的窗帘缝隙里挤进来。或许这就是鸟儿的起床号。紧接着,有两只、三只、四只鸟儿跟着鸣叫。很快,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将我彻底唤醒。
父母住的小区绿化得非常好,一到春天就满眼碧绿:最低处有草坪,往上是四季常绿的冬青,再往上是被修剪得圆鼓鼓的黄杨,然后是银杏、香樟、白玉兰等高大乔木,还有樱花树和海棠树。
我陪父亲在小区内散步时,总能看到站在枝丫上欢唱的乌鸫。最初见到乌鸫,我以为是八哥,因为它通体漆黑,且嘴是黄色的。乌鸫在我国,原系主要生活于长江流域的一种留鸟。古时候,人们把乌鸫叫作百舌鸟,因为它“笙簧百啭音韵多”,能使“黄鹂吞声燕无语”(刘禹锡《百舌吟》),可模仿出几十种鸟鸣,故由一只乌鸫的“花叫”,可欣赏到黄莺、布谷、云雀、八哥、画眉等不同鸟儿的叫声,堪称鸟中的“口技者”。乌鸫鸣叫时,黑尾巴一翘一翘,黄嘴一张一合,或呱咕呱咕,或叽啾叽啾,或咿喂咿喂,或喔唷喔唷……
小区里还有喜鹊、珠颈斑鸠、啄木鸟,它们或在灌木丛中窸窸窣窣地走动,或在草坪上振翅寻找食物,或歪着头清理羽毛,或腾挪翻越练就躲避敌人的技巧……
对于鸟,我最熟悉的莫过于珠颈斑鸠、黄毛鹦鹉、虎皮鹦鹉、鸽子、麻雀——父母曾喂养过这些鸟。从前,家中老宅有个小院,不大,但摆些母亲种的花花草草还是绰绰有余的。母亲还让心灵手巧的二舅在院墙的东西两边打眼,用膨胀螺丝固定住两根被焊成90度的角铁,在角铁中间再放上一根手指粗的钢筋,专为挂鸟笼所用。母亲的这个办法让馋嘴的猫儿只能望鸟兴叹。那时,我每天早晨都会在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
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花、鸟是“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他认为种花养鸟要融入自己的情感:“夜则后花而眠,朝则先鸟而起”,“及至莺老花残,辄怏怏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谓不负花鸟;而花鸟得予,亦所称‘一人知己,死可无恨’者乎”。他把花、鸟当作有感情的知己,喜爱花鸟到了痴迷的境地。
父母都极其喜欢鸟儿,从不舍得让这些鸟儿在院内过夜,即便是后来二舅又为它们搭上了能遮风挡雨的棚子。喜欢早起的母亲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将六个鸟笼子从屋里拿出挂到架子上。偶尔刮风下雨,母亲故意将它们留在房间里。它们就使劲地叫,仿佛是在提醒母亲快快把它们请到院子里去。喂食、喂水、收鸟笼则是父亲的事,一年四季从不间断。我记得在三伏天的中午,怕热的父亲总是头戴草帽给鸟儿喂水,精心呵护着它们。我曾问父亲这么做图啥。父亲说,他就是喜欢听鸟儿的鸣叫,鸟鸣声声悦身心,鸟儿的鸣叫是天籁之音。说来也怪,这些鸟儿一见到父亲就特别爱叫,尤其是在喂食的时候,就像撒娇的孩子一样叫着、跳着,将谷子弄了一地,引来无数麻雀争相啄食。每年母亲都要为此多买好多的谷子。
如今,因为我的孩子去市里读书,父母离开了久居的老宅,搬到这个小区替我照顾她的饮食起居。我在县城里工作,有空就去看他们。临走时,母亲将黄毛鹦鹉、虎皮鹦鹉连同剩下的谷子一起赠予老邻居,把珠颈斑鸠、鸽子送了乡下的一位养鸽专业户。值得庆幸的是,父母现在的居所仍有鸟语花香,他们还能时时听到鸟鸣声。
昨天,我看见一只肥硕的珠颈斑鸠落进了老宅的小院里,久久不肯离去。我试着走近,它不仅没飞走,还冲我“咕咕”叫,可惜我当时没有谷子喂它。鸟鸣声声悦身心。我感觉它非常眼熟,可能就是父母以前养过的那些珠颈斑鸠中的一只。它也知道常回家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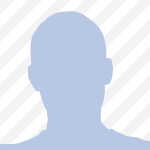







评论